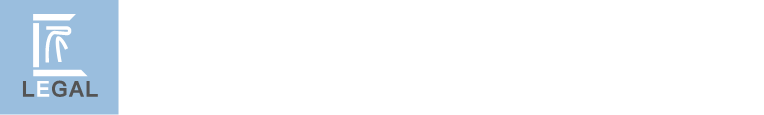让商业法律通俗易懂
最近,原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据说他的落马和一个案件有关,本着学习的态度,笔者研究了这个案件。
事件经过
2005年,博智资本与鸿元公司(原名亚创公司)签订《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约定由鸿元公司作为博智公司的托管人并代表博智公司持有新华人寿9%的股份,而博智公司将为此向鸿元公司支付年托管费(年费),资金由博智资本提供。因博智资本为外资,国家对外资持股保险公司有股权比例限制,双方担心《委托投资及托管协议》无效,又另外签订其他协议明确协议一旦无效的后果及责任承担。
2009年,双方协商解除代持关系,但未协商成功。博智资本要求鸿元公司向指定第三方转让股份,鸿元公司不予回应。
2010年,双方决定将代持的9%股份全部转让给第三方,并签订《股份及权益转让协议》,第三方分别向博智资本、鸿元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21.6亿、7.02亿。
注意!就是这份协议其中一个条款,使得这场官司在一开始就注定了败局。
从2012年开始至今,博智资本败诉后再换案由起诉,换了5个案由后仍以失败告终:
2012年,博智资本起诉鸿元等公司股权转让纠纷,北京高院判决支持了博智资本诉请。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委托投资与股权归属是两个法律关系,委托投资方对委托投资的股份不一定有所有权(这个观点感觉有些一言难尽,有兴趣可以去看下判决原文),于是撤销北京高院的判决并驳回博智资本的起诉。这个改判,据说是与最近落马的高官沈德咏有关。
很明显,这个条款把博智资本与鸿元公司之间一揽子关系作了终结。即使鸿元公司与博智资本之间的代持、托管关系有效,但此刻该条款对双方的关系及款项重新进行了约定,而这个最终文本未有任何代持或代收款的表示。
这一条款为何出现在这份协议中,有几种可能:
一是这个条款是博智资本的真实意思,只是后期反悔。这种可能性不大,毕竟7亿的案件标的,每次起诉诉讼费的诉讼费都要三五百万,还不算律师费;
二是这笔交易可能是领导层之间基于信任而确立的,大框架既已确定,协议只是走个过场没有细看;
三是协议可能是由经验不足的人员起草的,起草时套用模版,对模版上的某些条款未进行深究,毕竟套用模版这个事情都可能出现在B站的招股书上。
所以,我一直认为律师应该兼具诉讼经验和非诉经验,二者互为补充,没有诉讼经验的律师写协议时,可能不清楚每一个条款背后可能隐藏的歧义、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不仅不能为赢得诉讼提供相应的“弹药”,还可能把客户带入坑;而没有非诉经验的律师,可能不能理解客户的商业安排,会把每一次调解或商务谈判变成你死我活的战场。